被绑架的盗火者
蒋方舟
(图片来自网络)
94年12月出生的程齐家,比周围的同学小一点。2010年,他在人大附中——这所声名远扬的名校读高三。
程齐家所在的是英语实验班,而他的强项是数理化。若是按部就班,最好的结局是他将会考进清华的机械专业,毕业后研究汽车。程齐家住校,每周末,他妈妈都会来看他,给全封闭环境下的儿子带来一些外界的社会新闻,让他多些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谈话交流、彼此安心。
高三就这样规律平静地过了一半。一个周末,程齐家的妈妈来看他,聊天中她说一位院士在深圳主持筹建了一所大学,准备招收已完成高中知识学习的高二学生,学生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高水平测试,进入大学后可以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老师们都是知名学者,这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只收高二的学生。学校官方的解释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但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真正用意:对直面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来说,考北大清华港大,当然是更顺理成章的目标。南科大从高二招生,当然是为了能拦腰斩断、收割优质生源。
程齐家后来回忆说:“南科大就是这样以一方净土的模糊形象被我所认知。当时我未把此事真正放在心上,妈妈也玩笑似地感叹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也只得认命,觉得水木塘边赏月、未名湖畔折柳亦不枉此生。”
年底,班主任拿了一份通知,说南科大将在人大附中高三年级招收第一届学生。程齐家当时已经获得了校荐北航的机会,也自荐报考了上海交大,虽然对南科大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他立刻觉得这是个惊喜,第一时间报了名。
对于要报考南科大的学生,人大附中不仅没有打压,让他们回归官方志愿,反而给予了让人意外的热情鼓励。除了几次动员,人大的刘校长还专门给想报考南科大的家长开了个见面会,会上和南科大的新校长朱清时电话连线,解答家长的问题,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这次见面会之后,人大附中一共有7个孩子,确定了报考。
朱清时校长的演讲一向犀利而昂扬,“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去行政化”这样的词是屡试不爽的鸡血,而他描述的南科大蓝图更像近在咫尺的乌托邦。朱校长说首届招生时只招50名学生,未来亦将严格把师生比控制在1∶8的规模,小班化教学是教育模式的回归。大一、大二采用通识教育。
可是在对家长的说明会上,却不知道朱校长有没有说明,南科大还没有获得教育部颁布的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也没有招生许可,大学毕业后的文凭也可能得不到国家承认。
在咨询会结束几天后,教育部终于向南科大颁发了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这所先斩后奏的大学,方才获得了迟到的准生证。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按照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
人大附中特意为南科大自主招生的笔试开设了考场。考试的题目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考数学、物理和英语,题目比高考要难。
这三门课是程齐家的强项,他考完之后就对母亲说:“绝对没有问题。”
通过笔试的,除了程齐家之外还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比程齐家成绩要好一些,性格内向,出于顾虑,最后放弃了南科大,冲刺北大清华。
通过笔试之后,程齐家就读南科大的意愿更加坚决,它不再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而是未来本身。
因为儿子的坚决,家长也开始衡量报考这所大学的风险。有的朋友坚决反对,说“中国政府的事儿你也信?”
风险当然是有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政府决策很容易变,“有时候领导换届了,往往一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南科大的重要推动者是深圳市,也是它的投资人。南科大的前途当然是随着业主更迭而瞬息万变的(后来事实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支持南科大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在今年五月因为贪腐而判处死缓)。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自授学历和文凭,家长反而并不太担心。“自授学历”是朱清时校长口中的高校恢复活力的关键。他说全世界唯有中国是国家学位,各个学校拼命去跟教育部公关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本末倒置,必须打破铁饭碗。
而家长确实也有更现实的考量。程齐家的妈妈认为对孩子来说,大学不会是学历的终点,他一定会继续深造,但总应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吧。
衡量之下,报考南科大,最好的结果是,程齐家接受了招生简章上承诺的高质量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
最坏的结果是学校解散了,他再回家来参加明年的高考——程齐家说,即使这样他也认了,大不了回来考清华。而他即使明年回来高考,也还比应届生小一岁。
寒假,正月初十前后,南科大在深圳进行了第二轮录取考试。程齐家第一次坐飞机,他自己飞。他是唯一单刀赴会的学生,参加了面试、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
两三天后,南科大打电话,祝贺录取。还没有开春,程齐家就早早告别了如临大敌备战中的同学们。
二月底,程齐家一个去了南科大报道,他带了几本书,包括易中天的《看不懂的中国人》,还有字帖和德语书——这些都是他准备上大学后自我教育的内容。
空旷崭新的校园里,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也许还没有赶来抢新闻的记者多。学生的组成乍一看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一支正规军。
——南科大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前一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这些孩子本来就是特殊的,他们像是从一个试验皿跳进了另一个,而南科大的校长朱清时是中科大的原校长,两个试验皿也属同胞。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高考考了566分,在去年九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除了他之外,南科大的首批新生里还有13岁的王嘉乐、岳照,14岁的范紫藜。
南科大在喧嚷中开学,晚上才得安静。学校安排学生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而是寄宿学校里一群难缠的问题学生,被音乐老师感化,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才能被唤醒,心灵变得温驯美好
放这部片子,大概是因为校长猜到了这会是一群难管的学生。他们年纪尚小,早早就被周遭目为神童,过早觉醒,天生反骨,又在外界对南科大的好奇中收获了许多注视。对南科大的天才们,除了教育,大概还有些教化的工作要做吧。
《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里唱:“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以后的日子。”
在广州黄埔军校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正式开课。
程齐家笼统而乐观总结他上大学后的感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了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冲到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四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六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五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六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
“学术自由”和“行政指挥”抗争的战役历史上早有过,且前者赢了。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大张旗鼓地要求统一动作。当时在云南的西南联大,也被要求实行毕业总考制。虽然其他学校也有牢骚,但只有联大全校一致抵抗。在这项规定实施的头两年,联大是唯一一所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教授也对学生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历史和现实如此相似,是因为被挑战的那一方只能见招拆招,路数如此单一。当时的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相要挟。西南联大仍然自行其是。最后,教育部无法,只能作出保全脸面的妥协:联大学生需参加考试,但是全部自动通过,联大不必把分数上报给教育部。到了1941年,联大干脆连过场都不走了。
七十年前,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因为“学术独立”是学校和执政党谈条件的共同底线。是时,知识精英还有寡头集团的话语权。如今,物是人非,角力的双方不同,赢面自然不同。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
“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得可怕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打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的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孩子们沉重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被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宏亮激昂的调门地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总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的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想毕了业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象得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刊载于《信睿》
7-8月刊 蒋方舟专栏“九年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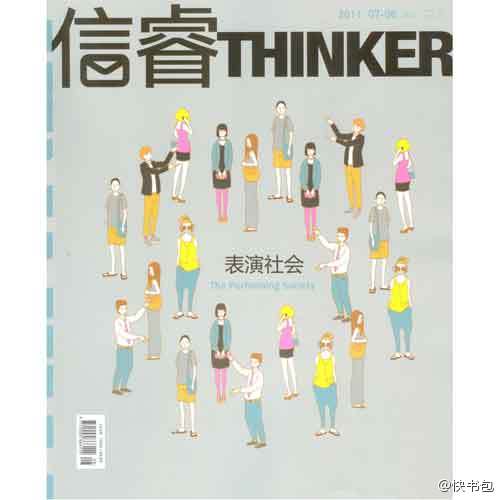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